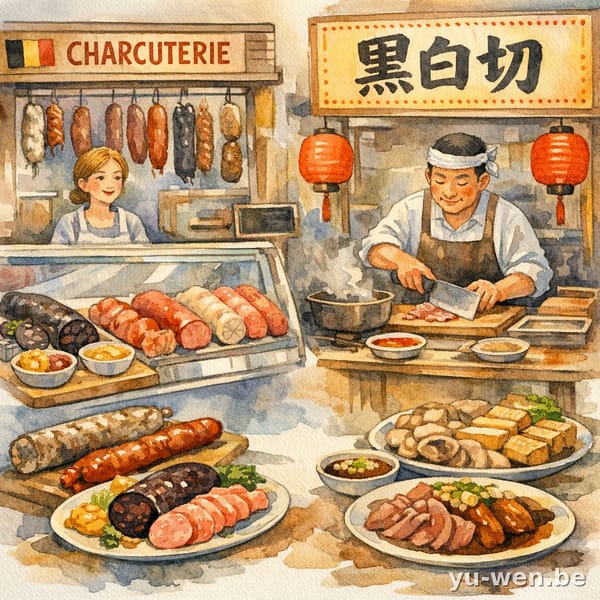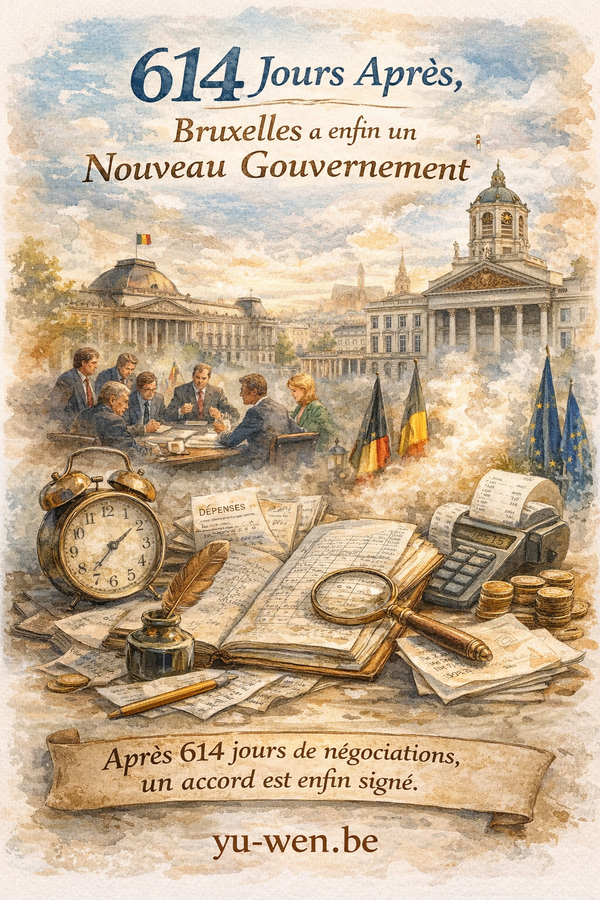比利時的廁所通行證與尋廁文化
在比利時,廁所不只是空間,更是一種權利。從克隆氏症協會推動的 Toiletpas,到尋廁 App、公共設施與成人紙尿褲的現實抉擇,這是一篇關於城市如何接住身體的故事。

「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。」— 維克多·雨果。
那天我在布魯塞爾街角急急找廁所時,忽然懂了這句話。原來「文明」有時不是歷史建築,而是一扇願意為身體打開的門。根據數據調查,歐洲老年人常常因為如廁的優雅問題,漸漸不願出門,晉而造成社交恐懼症。
從「尷尬」開始的制度
因此,比利時開始提倡一項低調卻溫柔的制度,叫做 「廁所通行證」(Toiletpas / Carte Urgence Toilettes)。
它由 克隆氏症與潰瘍性結腸炎協會(Crohn-RCUH asbl、CCV-vzw)推動,讓患者能在緊急狀況下出示證明,於合作店家、餐館、零售點快速、免費、低調地使用廁所。
申請需醫師證明,協會會員通常可免費取得;卡上附有持照者姓名與照片,並以法語、荷語、英語三語標示,讓跨區或跨國旅行時也能被理解。
它尚未是全國性法令,而是一個由信任支撐的合作網絡。餐飲與零售公會(如 Horeca Vlaanderen、Comeos、Unizo)自願加入,讓善意有了制度化的入口。
一張小卡,讓城市說:「我懂你現在的急。」
小門卡,大文明
台灣的公共如廁資源更為密集且多為免費,捷運與便利商店尤其顯著;但在「特定需求者的通行權」這件事上,比利時的做法提供了另一種啟發。公共不只是「人人都能進去」,也是「在需要時能被快速優先接住」。一邊是量與普及,一邊是權利與保障,兩者不衝突,反而能互補,讓城市更可居。
普通人也會遇到的「尋廁時刻」
即使你不是通行證使用者,在比利時找廁所仍是一場小冒險。公共廁所數量有限,店家也沒有義務開放,
「找到、進去、體面離開」成了城市生活的三步曲。
📱 在比利時找廁所可用的 App
對旅人而言,手機地圖就是現代版的「如廁羅盤」。目前在比利時仍可穩定使用的兩款 App 是 HogeNood 與 ICI Toilettes。它們一個誕生於荷蘭,一個源自法國,
卻都延伸出了歐陸式的公共廁所地圖文化——不是炫技,而是把「急」轉化為資訊的溫柔。
| 名稱 | 適用範圍 | 最新狀態與特色 | 優點 | 注意事項 |
|---|---|---|---|---|
| HogeNood | 荷蘭、比利時全區皆可使用 | 仍在 Google Play 與 App Store 上架,2025 年 7 月更新。可查公共與私人廁所,含無障礙資訊。 | 資料庫穩定、介面簡潔、離線模式實用。 | 部分地點由使用者上傳,資料更新速度依區域而異。 |
| ICI Toilettes | 法語區(比利時南部)與法國境內 | 2025 年仍運作良好,版本持續更新。支援評價、照片與「免費/付費」篩選。 | 使用者社群活躍、資訊具在地回饋。 | 在荷語區(如安特衛普)涵蓋率略低。 |
建議同時安裝兩款:
HogeNood 負責找「哪裡最近」,
ICI Toilettes 讓你知道「哪裡最乾淨」。
若兩者皆無結果,請回到古典策略——
圖書館、市政廳、百貨與咖啡館,永遠是城市的體面出口。
當城市太慢、身體太快:成人紙尿褲的現實可行性
沒有人願意在包裡放一包成人紙尿褲,但當城市的速度慢於身體的需求,它確實是一種務實的保險。
在歐洲,醫師偶爾會建議慢性腸疾或高齡旅客於長途交通、演出或大型活動時使用,目的不是「放棄控制」,而是減少焦慮與突發的風險。比利時藥局可買到輕薄、無味、服貼的款式(如 Tena、Hartmann、Abena),多數外觀近似內衣,可搭配寬鬆衣物使用。
然而,它應該是備案,而非常態。真正的文明,不在於我們多會掩飾生理現實,而在於城市是否願意為這份現實留門。
一張通行證、一扇門、一層紙的防護,
都是同一個願望:
不被羞辱地活在公共空間裡。
城市的柔軟,藏在門後
某天我在布魯塞爾,手上沒有通行證,也不想狼狽。我點了一杯最便宜的濃縮咖啡,微笑著問:“Excusez-moi, puis-je utiliser vos toilettes ?”
店員也笑,指了指通道,那一刻我心想——城市也許沒有擁抱我,但它讓我留下體面。
我把這些經驗記下來,不是因為我永遠能「鎮定如女王」,而是因為在天氣冷又多雨的比利時,知道下一步在哪裡,就少了一分狼狽,多了一點餘裕。
當身體說「現在」,
而城市能回答「請」,
我們就都贏了一場小小的文明戰。